49da5195-aef0-4387-bdfb-b2276d69dbd0.jpg)
49da5195-aef0-4387-bdfb-b2276d69dbd0.jpg)



“天空之上,还有什么?”水幕中央,一位手捧建盏的少年仰首,对着浩瀚夜空,发出穿越八百年的叩问。
这一问,如电光石火,猝然劈开历史厚重的层云。随光幕流转,那个在教科书里被简化为“南宋理学家”的名字——朱熹,在这一刻血肉丰满地向我们走来。
山水与哲思相遇,月光与舞台交融。这不只是一场演出,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,一次在山水之间寻回本心的精神之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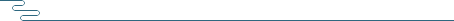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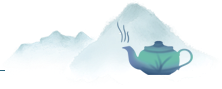
初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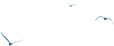
山水有门,叩问千年
少年的问题悬在空中,仿佛在敲打着每个现代观众的心扉。在信息喧嚣、步履匆匆的今天,这份对苍穹最初的好奇,仿佛早已遗失。
朱熹在《朱子语类》中尝言:“大抵观书先须熟读,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;继以精思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然后可以有得尔。”
而此刻,观众面对的已非书本,而是整个被搬上舞台的天地。
武夷山的三十六峰、九十九岩,在精密的光影技术下次第浮现、旋转、聚合。它们不再仅仅是地质奇观或风景名胜,更像是一部部缓缓打开的无字天书。
丹崖赤壁、九曲清溪,不再是静止的背景,它们活了过来,成为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鲜活课堂。
他观水,见其昼夜不息,便悟出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时间哲学与生命感喟;他看山,见其巍然不动、滋养万物,便领会“仁者乐山”那份敦厚、静穆与担当。抽象晦涩的理学概念,褪去故纸堆的尘埃,如此直观地化作可触可感的山水呼吸。
朱熹用了近五十年的光阴,徜徉、栖居、阅读武夷山水,将自然造化与心中义理相互印证。

朱子徜徉、栖居武夷山水
而《月映武夷》这场演出,则试图在七十分钟内,为观众推开那扇通往理学堂奥的门径,寻求蕴藏在这寻常的“山水动静之间”的“道”。
正如朱熹的诗:“问渠那得清如许?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这山水,便是那永不枯竭的思想活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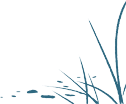
沉浸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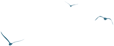
石火“字”光,理在人间
真正的舞台魔力,在于能将最抽象的思想,淬炼为可感的光影与震撼的场景。
“逝者如斯”“智动仁静”这些镌刻在真实武夷山摩崖峭壁上的朱红大字,经由现代科技手段,在舞台上被重新“唤醒”。它们挣脱了石壁的束缚,在空气中流转、放大,仿佛带着八百年前那位哲人落笔时手的温度、心的激荡。这不再是后世瞻仰的冰冷遗迹,而是思想迸发那一刻的现场重现,是穿越时空直接与灵魂对话的哲学符号。
其中,对“天理”的诠释尤为撼人心魄。
剧情行至深处,黑衣使者代表官方权势,厉声斥责朱熹之学为“伪学”,直指其为“伪学魁首”。雨幕倾泻而下,老年朱熹立于滂沱之中,白发披散,衣衫尽湿,然而他的眼神却比窑中烈火更加灼亮。他仰首向天,声若洪钟:“我一生所求所守,无非天地间一个‘理’字!”
许多人口中常说的“岂有此理”“没天理”,在这时找到了它沉甸甸的历史与哲学源头。
演出并未坠入枯燥的哲学说教,而是巧妙地将“天理”掰开揉碎,具象于武夷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之中。那历经千万年风雨冲刷而岿然屹立的千仞丹崖,体现的是“坚韧不拔”之理;那九曲溪水,遇巨岩则灵巧绕行,于平缓处则蓄势深流,诠释的是“刚柔相济”之理。
水幕之上,山石的纹理与建盏名品“兔毫盏”中丝丝缕缕的釉色花纹交错融合,潺潺溪流竟幻化组成巨大的“理”字笔画。
此情此景,让人们豁然开朗:天理,绝非高高在上、玄奥莫测的教条,它正是这山川大地、万物生灵内在的运行法则,是蕴藏于日常中的做人底线与处世智慧。
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阐释“格物致知”,强调的正是即物穷理,今日舞台,可谓是对此最生动的视觉注解。
同样被赋予人间烟火温度的,还有“礼”。
上元灯节一幕,纸扎的龙鱼道具欢腾地从观众席间穿梭游过,乡亲们手提灯笼,簇拥着、呼唤着朱子为“先生”,请他主持村里的成人冠礼。这一幕,生动演绎了朱熹如何以其所著《朱子家礼》,深刻改写了西周以来“礼不下庶人”的千年陈规。
舞台上,即将成年的少年们身着寻常粗布衣裳,跪拜的是用本地蒲草亲手编织的蒲团,祭祀案几上摆放的是山中风物。没有钟鸣鼎食的贵族奢华,却在简朴中流淌着无比的庄重与诚敬。
朱熹的实践,正在于他将原本局限于庙堂高阁的繁复礼仪,成功地“翻译”成了寻常百姓在婚丧嫁娶、岁时祭祀中可循可依的规范,融入了烟火日子里的敬意与亲情。这份“礼下庶人”的温暖文化遗产,历经八百余年,至今仍在武夷山地区许多家族的成长仪式中得以传承与实践。

“礼下庶人”的变革
而让朱熹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的,则是那一块块看似沉默的雕版。舞台设计匠心独运,整体倾斜至六十度,瞬间化为举世闻名的建阳书坊的巨大雕版。演员们化身刻工与文人,以身体为笔、为刀,在倾斜的版面上艰难而专注地起舞、刻画。

建本印刷技艺,曾让建阳成为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一
光影交错间,一段关于“建本”的历史被娓娓道来:两宋时期,福建建阳麻沙、崇化等地,书坊栉比,刻工如云,全国出版书籍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源于此地,号称“图书之府”。不仅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等理学经典藉此流传天下,连最早的《西游记》刻本也诞生于此。
这流传千古的墨香,并未尘封于历史。今日,在武夷山的有轨电车上,常设有建本拓印体验区。孩子们用毛刷蘸墨,于复刻雕版上轻轻一刷,再覆纸按压,朱熹“少年易老学难成”的诗句便跃然纸上。古老的“建本”技艺,正以如此鲜活灵动的方式,将文明的种子,悄然播撒进当代人的心田。

共鸣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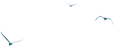
山水是我,赤子同归
演出的情感高潮,无疑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自我对话。
老年的朱熹,面容清癯,须发如雪;少年的朱熹,眼神澄澈,满怀憧憬。两人隔着一道由光影构成的、象征九曲溪的潺潺川流,遥遥相望。他们同时开口,声音重叠,似回响,似问答:“我和我隔川相望……我和我别来无恙。”
这不仅仅是朱熹对自己一生的回眸、审视与最终的和解,更像一面澄澈的镜子,映照出人们内心的自我叩问:那个曾经对世界充满无限好奇、勇敢而纯粹的“少年我”,是否还在生命深处某个角落?在岁月的奔波、现实的磋磨中,是否早已遗落了最初的梦想与本真?
演出里,镌刻在五夫紫阳楼里的“不远复”三个字,如水中之月,温柔而坚定地从光影溪流中浮现出来。此语出自《周易·复卦》:“不远复,无祗悔,元吉。”
在演出中,从少年朱熹跋涉千里、求师问学,到老年朱熹身处逆境、困守初心,其一生行迹无不在诠释着“不远复”的真谛。它仿佛一声穿越千年的呼唤,给予所有身处迷茫或倦怠的现代人一份珍贵的底气:人生之路,偶有偏离并不可怕,重要的是内心始终保有那份“归返”的清醒与勇气。

朱熹求学的六经堂,是屏山书院前身
白鹭,是武夷山水间常见的精灵,是古典文学中象征高洁、超逸的君子意象。在《月映武夷》中,成为了连接天与地、古与今、台上与台下的诗意桥梁。
当白鹭飞翔,舞台的物理界限彻底消失,观众不再是戏剧的旁观者,而成为与朱熹、与武夷山水、与千年不绝的文脉共同飞翔的参与者。这只幻化的白鹭,最终将所有纷繁的思绪与情感,引向那首主题曲《天心一念》悠扬而深邃的旋律之中。

领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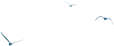
月映万川,光照来路
“明月就是天心映在千江……”当《天心一念》的歌声悠然响起,那些在演出中精心铺陈的“文化彩蛋”,如散落的珠玉被旋律的丝线一一串起。

天心一念主题曲,藏着许多成语
“出将入相”四字,道尽了朱熹身为文士却心怀经世济民之志、文武兼济的人生理想;“轻舟千帆”的意象,既呼应了九曲溪的秀丽风光,也暗含了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历史豁达感;而“万紫千红”更是直接源自朱熹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春日》: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
古老的成语在当代的乐章中被重新赋活,歌词本身就如同一部微缩的理学诗典,让观众在音乐的美感沉醉中,完成了一次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深情温习与自然领悟。
这一切艺术表达的终极指向,正是朱熹理学思想中“月映万川,理一分殊”的至高境界。天理如同一轮皎洁的明月(理一),无私地普照整个宇宙;而世间的万千事物,如江河湖海(分殊),虽形态、大小、清浊各不相同,却都能映照出同样一轮完整无缺的月影。

在万川归一中邂逅朱子
朱熹的思想就如同这亘古不变的月光,平等而慈悲地照进每一条生命的河流。它不带有强迫的意味,只提供清澈的映照;不进行生硬的说教,只给予智慧的启迪。
最好的文旅融合盛宴,从来不是简单的声色光影之娱,而恰恰是这种自然奇观与人文深度的共鸣,是古老传统与现代表达的创造性交融。

演出现场,观众气氛热烈
正如学者蒋昌建在观后所言:“看完这场演出再去看武夷山,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山;再去理解朱子,那一定是不一样的朱子。”因为看山的眼睛,已被文化的汁液浸润;理解古人的心灵,已在那一刻与先贤达成了跨越时空的共情。
这,正是文化传承最美的姿态与模样。它让八百年前的理学,不再是古籍中僵硬陌生的文字,而是可感如头顶的天心明月,可触如眼前的青山白鹭,可循如内心的赤子初心。
在《月映武夷》这部光影诗篇中,人们不仅深情邂逅了那位有血有肉的朱熹,更重要的是,在山水与哲思的共鸣中,遇见了那个更加澄明、更加丰厚、也更充满内在力量的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