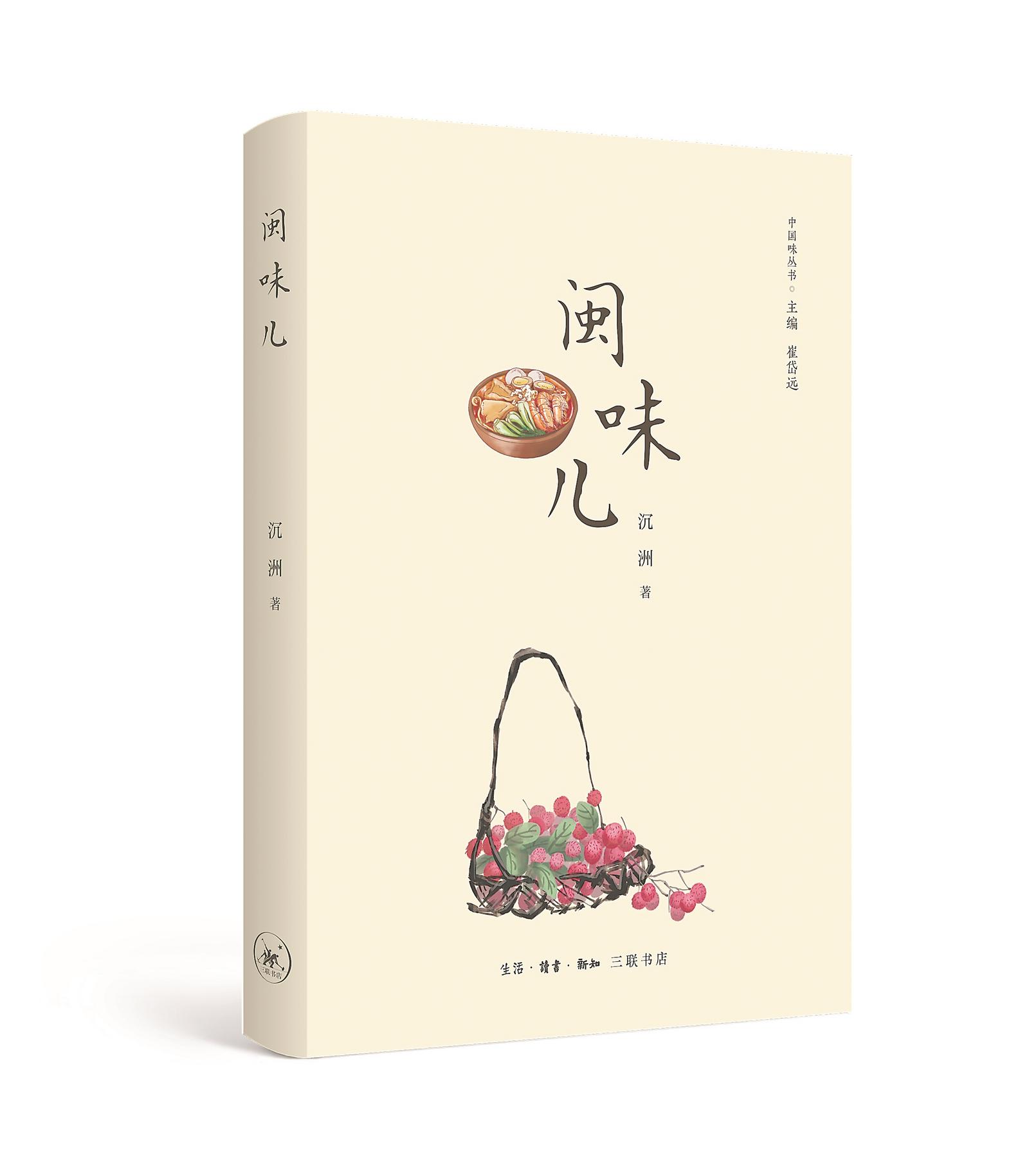
八闽地理单元封闭,负山面海、山岭崎岖、江河纵横,历史上开化较迟。西晋末年以来,北方游牧民族数次入侵中原,社会动荡,衣冠士族开始迁徙入闽避祸,先进的农耕文明光照闽地。
饮食能折射一个地域兴衰,闽都是闽菜发源地,作为旗帜的福州菜系迟至清末方渐具雏形,因此有机会汲取粤菜和浙菜之长,进而跻身中国八大菜系之列。
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,对外省朋友说起闽菜,除了佛跳墙、全折瓜、爆炒双脆,再凑上扁肉燕、鱼丸、鼎边糊这些大众小吃,便再难开出菜单。究其缘由,绕不开八闽特殊的地理情状。因为立地海防前线,福建自20世纪中叶便鲜有发展,经济文化均落后其他沿海地区,吃喝之事无以兴盛。闽菜食材纯天然,野生稀有且不成规模,端上台面的价格自然不菲,很多人就没正经吃过。
福建当年的交通局促,颠簸进来一些客人,把那些吃到嘴里不地道的闽菜概括为“酸酸甜甜、黏黏糊糊、汤汤水水”,闽菜在大众心里式微了。
其实,那个时期正值闽菜中兴,墙内开花墙外香,多数人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那些年,闽菜大师北上钓鱼台国宾馆,主厨外国元首欢迎宴;南下港澳、东南亚,展演传播精湛厨艺;参加首届全国烹饪技术竞赛……一次次力拔头筹。
细究起来,地理环境的限制,正是闽菜后来居上的底气之一。福建西北部横亘着高亢的武夷山山脉,挡住第四纪冰川南下,使得全域动植物种质资源丰富。境内从山地、丘陵、盆地、河谷、台地、平原到港湾、半岛、岛屿,多样的地貌形态成为各种动植物生长的天堂。浅海滩涂螺蚌蛏蛤,大江河湾鳞甲水族,山坳林间麂鹿獐兔,南部平原四时瓜果……这构成了足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闽菜食材。
闽菜以烹制山珍海味著称,在色香味形俱佳基础上,尤其以香和味见长,形成清鲜、醇和以及汤路广泛的风格。闽菜肇始于闽都,闽东、闽南、闽西、闽北、莆仙五地加盟,勾画出了闽菜的世系图谱。
闽菜食材组成众多,通常用的不是大众食材,还讲究地产。它不像鲁菜的面食,也不像川菜中的水煮鱼和畜肉,可以通过运输推广、普及,或从当地获取同类食材来攻城略地。闽菜赴异地烹饪表演,除本土食材,时常连水都要桶装带去。
正宗闽菜强调食材来源地道,佛跳墙的海参、瑶柱、花胶、花菇等一干物品,传统做法有严格产地选择;鸡汤汆海蚌的蚌,得来自漳港;淡糟香螺片的香螺,必须生长于长乐沿海;红糟非要闽侯、古田出品才能让大厨心里踏实。
在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里,从孩提时果腹充饥到后来笑纳八方饮食,我接触过不少菜肴。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,跟随父母工作调动,从内陆山区迁往沿海城市,求学和工作又定格在闽都。这数十年来进过嘴的,在闽菜系统有很大跨度,以这样的个人记忆体验来切入,选择有意思的山海食材,辅以独特的烹调技巧,再从容讲述一道道菜肴和个体的交集,好像会更有温度、更接地气。在大致说清菜肴前提下,强调对味与形的个人感受,再去追寻和挖掘美食背后的文化意味,这是我喜欢的角度。闽菜食材富于地域性,人们可以通过对稀有食材的获取认识它们,增长动植物知识,这些是构成美食不可或缺的部分,譬如黄瓜鱼、田鼠、福鼎芋的生长地域及特性,讲起来也饶有趣味。
还可以揭秘某些饮食形成原因,这常常是无心插柳的一种偶得,历经时间大浪淘沙,便堆出了文化层。譬如,福州人为何尤其喜好酸甜口味,与独特地理、气候有何关系?擂茶、涮九品这些药膳兼济的菜肴,又为何是客家先民在南迁路上和日常劳作中的发明?而烧卖和米包子这一类非面皮包馅食品,则烙有南迁士族对北方故土的乡愁印记。
通过记忆串联当下美食,在时光流淌中,我们被历代能工巧匠的执着和坚守感动,也痛心于商品经济下诚信体系的走失。饮食行当不仅需要技艺,商家良心也不能缺席。受大环境污染和滥捕滥杀波及,那些地道食材的情状每况愈下。濒危漳港海蚌的种质资源受到保护,却因此无法走向大众餐桌;地产香螺奇缺,只得改用次一级的红螺替代,而红螺现状也堪忧。
市场秩序不规范,以次充好大行其道,绿色养殖被低端高产绑架,那些方兴未艾的反季节大棚蔬菜,那些长盛不衰的滩涂养殖海田,那些密匝匝的水产网箱……不遵循自然规律的强制丰产,对原汁原味的闽菜必定是灾难。曾经傲然世界的美食大厦,在风吹雨淋里,还能持续美轮美奂下去吗?
中国人已经丰衣足食了四十年,面对丰富有余而精致不足的食物,沾沾自喜只会耽误前程,我们有必要洞见瓶颈。唯其如此,今人才可能与古人坐在同一张桌前谈滋论味,华夏千年的烹饪技艺也才能绵延下去。
